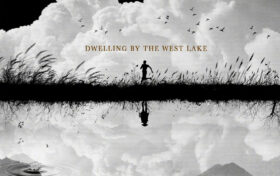当你一觉醒来,发现自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,你会怎么办?今年春节档的《人潮汹涌》(改编自《盗钥匙的方法》)就是基于这个设定,向我们展示了意想之外的互换人生。
电影中,因为一次意外,职业杀手周全和群演陈小萌互换身份,一时之间,单纯懒惰的陈小萌被迫卷入一场未知的谋杀,而思维缜密的周全却因短暂失忆重启人生。

《盗钥匙的方法》
同样,去年年底上映的《心灵奇旅》中,爵士演奏者乔好不容易获得了一次登台演出的机会,却意外掉进“生之来处”,成为了22号灵魂的导师。重新连接到尘世之后,一心想再度成人的乔变成了一只猫,对人类失去信心的22却钻进了乔的身体。两人穿梭在纽约繁忙混乱的街道中,从不同的载体重新体会到生命的火花。

《心灵奇旅》
《人潮汹涌》中两人互换身份的桥段为电影制造了许多笑料,也点明了“努力的人就算被丢进糟糕的人生也会变好”的主题;《心灵奇旅》则为我们熬了好大一碗“活在当下”的鸡汤。这两年,以“互换身体”为情节驱动的作品不在少数,却少有新意。所以,为什么导演和编剧们这么偏爱这一类设定?
“互换身体”梗是怎么来的?
早在1882年,美国作家F·安斯蒂就在小说《反之亦然》中提出了这个概念。男主角保罗和厌学的儿子迪克互换身体,他回到了熟悉的校园时光,而迪克则开始了自己向往已久的成年生活。这个天马行空、超现实的设定在随后的一些故事中延续下来,无论是夫妻双方互换,还是母亲和女儿,大多讲的是关系中的换位思考和相互理解。

《小爸爸大儿子》
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,好莱坞进入黄金时期,以往的浪漫爱情片、西部拓荒片,悬疑惊悚片等等似乎已被电影人和观众消遣殆尽。于是,“互换身体”这个有反转、能带动票房,还能满足观众内心需求的题材再度被提上日程。
1979年的《怪诞星期五》(后来分别在1995年和2003年重新翻拍)就是当时这一类型的标杆——单身母亲和青春期女儿,仿佛天生不对付,两人在一次争吵过后身体对换,引发了一连串啼笑皆非的故事。


《长大》
抛开戏剧冲突,“互换身体”对演员的表演功底也是一种挑战。很多时候特效帮不上忙,只能靠演员自身来完成互换前后的角色转变。
在1997年的科幻片《千钧一发》中,基因筛选是人类社会的第一法则。伊桑·霍克饰演的文森特就是一个有基因缺陷的“病人”,他通过和裘德·洛扮演的“正常人”杰罗姆身份对调,实现了太空旅行的梦想。电影从头至尾没有进行任何技术调整,而是给两位演员空间自由发挥,让他们自然流露出在社会达尔文法则前的无奈和绝望。


《千钧一发》
而在日剧新番《天国与地狱》里,热血刑警望月彩子在一次追捕行动中,和变态杀人狂日高灵魂互换,一觉醒来,“彩子”(高桥一生饰演)望着镜子中自己的脸,惊诧、愤怒、不甘种种情绪交织,两人互换后猫鼠游戏的走向悬而未决。


《天国与地狱》
但这些似乎还不足以解释“互换身体”梗的流行,甚至是滥用。在豆瓣评分6.7的电影《两男变错身》中,两位主角性别、年龄都相同,区别在于一个是事业成功、家庭幸福的工作狂,另一个是无业、无稳定伴侣且不打算长大的浪荡子。两人都对自己现有的生活感到厌倦,渴望拥有对方的人生。然而真的互换后,不适和荒谬迅速占据了他们的生活,也让他们反思起自己过往获得的一切。
或许我们就像《两男变错身》里的戴维和米奇,人类“想要更好”的思维和欲望让我们总是观望着他人的生活,眼花缭乱的同时,内心还在不停地挣扎——到底谁更好?到底我适合什么?到底我想要什么?
为什么我们总幻想成为另一个人?
《广告狂人》里的唐纳德·德雷普在一次去加州的旅行中曾说:“我们想要得太多,所以我们不完美;在得到那些梦寐以求的东西后,我们又怀念以前曾拥有的,所以我们那么容易被击垮。”唐纳德也是一个逃避自我、一心想要成为他人的悲观角色。他认为只要他活在另外一个人的壳里,就能躲避一切自身造成的灾难,忘记自己的缺陷。而推动这一躲避行为的,正是他的欲望。
欲望作为人动物性本能的一种,在接二连三的现实残骸里,刺激我们去寻找下一个可能的希望。弗洛伊德在他最早的心理分析学中提出:人的行为驱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欲望。
婴儿想要一个玩具,是因为他的欲望在告诉他,玩具代表快乐;成年人想要更多的财富,因为他们的欲望说,财富是安稳、是地位。欲望犹如一个巨大的指南针,在碎裂的现实里,为我们指点一个明确又安全的方向。而到了当代,这个方向变成了远在天边、又近在咫尺的“那个人”。


《天国与地狱》
进入社交媒体时代,人们的生活正逐步变成一个个信息,通过网络扩散到世界各个角落。在朋友圈,我们总能看到发文必配九张图、过着几乎完美的生活的“那个人”;在微博上,“那个人”一夜之间成为博主,一条微博的转发量能与东欧国家人口相比较;
而在国外社交媒体上,TA通常身材如雕刻,漫步于巴黎街头,或是坐着直升飞机在纽约上空喝香槟……就像《人潮汹涌》中见财起意的陈小萌,现实生活中的我们被残缺的信息挟持,被片面的完美收购,所以我们想成为我们眼中完美的“那个人”。
除开欲望的操控,“想”也源自人本能的怀旧,和对当下生活的不满。怀旧一词“nostalgia”来自希腊语,本意是“旧伤口的疼痛感”,这种疼痛感或许会因为时间淡化,但它就像回忆,会一直停留在脑海深处,挥之不去。
不满情绪来自生活的种种细节,它可以是早上没清理干净的厨房水槽,也可能是意料之外的下雨天、忘记充电的手机。这些平日里小小的“不满”,日积月累后成为一种消极情绪,为我们戴上一副冷色眼镜,不仅让我们在看待事物时失去了那份乐观和希望,还不断替我们做出假设——“如果那样,就好了”。
在《长大》里,12岁的乔什个子太矮、相貌平平,不能追求自己心仪的女生,他在游戏机中投入25美分,许愿自己能马上变成大人。第二天,乔什愿望成真,成为大人后的他如鱼得水,工作爱情双丰收。但生活的压力一点点累积,已经成年的他又迫切地想回到12岁,重新体验那份天真和无忧无虑。


《长大》
小孩和大人,这两个自然规律的产物始终在与对方进行着无形的较量,如同我们和“那个人”,大家都相互嫉妒着、渴望着,真的互换了又彼此同情。小孩想成为大人,因为他们想要长大,这样可以不用上学,拥有独立的人生,而大人们想成为小孩,因为他们想暂停、想获得单纯生活,卸下沉重的责任。
他人镜像中的我是什么样子的?
认知心理学中的社会认知概念提到,在当代社会这个交流性极高、互动性极强的群体里,我们从他人的角度,或从他人的身份、性别、阶层能更好认知自己的价值。人是一种拥有同理心的高级动物——朋友遭遇苦难时我们会给予帮助;情侣争吵后会站在对方角度反思,自己做错了什么。


《翱翔于天际的夜鹰》
就像《广告狂人》中,贝蒂发现唐纳德的真实身份后决定要离开,唐纳德苦苦相求,几乎绝望的贝蒂说道:“如果你是我,你会爱你自己吗?”这类生活中常见的“换位思考”正是同理心,是我们理解他人、面对世界的一种有效心理实践。在这种实践当中,我们会跳出自己的惯性,进入另一种陌生的思维模式,对同一个问题进行换位思考,给出更加客观理性的回答。
在这些故事的最后,主角回到自己的身体/身份后通常会十分释怀,仿佛泡进温水池。“互换身体”看似是一个能带来乐趣和挑战的人生重启键,但这重启背后是“从无到有”的二次建设,看似充满希望的二次人生实则也是由无数个未知推积而成。
我们无法保证未知的结果是否乐观,也不能肯定它能满足我们的欲望和需求,但唯一能确定的是,在互换后我们更能感知自身的美好和当下的可贵。“我”眼中的自己也许处处不如意,但他人镜像中的“我”却总有可取之处。就像在《人潮汹涌》中,杀手周全失忆后迅速接受了陈小萌的身份,并开始着手研究演技、改善生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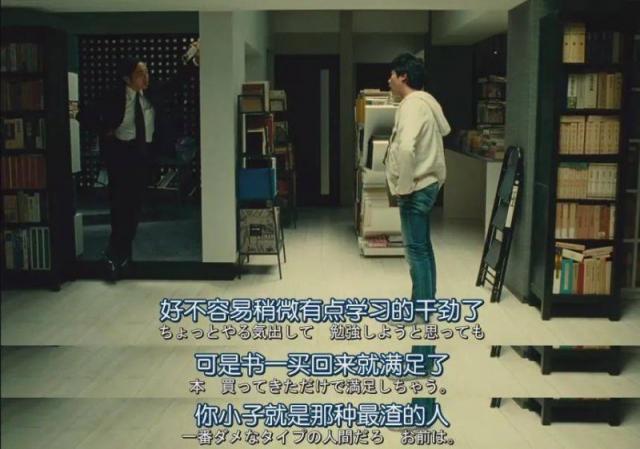
《盗钥匙的方法》
“人畜其实同理,轮回何须六道?”莫言在《生死疲劳》中写道。《生死疲劳》中的主人公西门闹含冤而死,落入阴曹地府后他重生为驴、牛、猪、狗和婴儿。几世之间,他忙着生,忙着死,忙着用不同的身体体验时代变迁,最后他成为了一个旁观者——以什么身份活着,真的有那么重要吗?

 微信扫一扫打赏
微信扫一扫打赏
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
支付宝扫一扫打赏